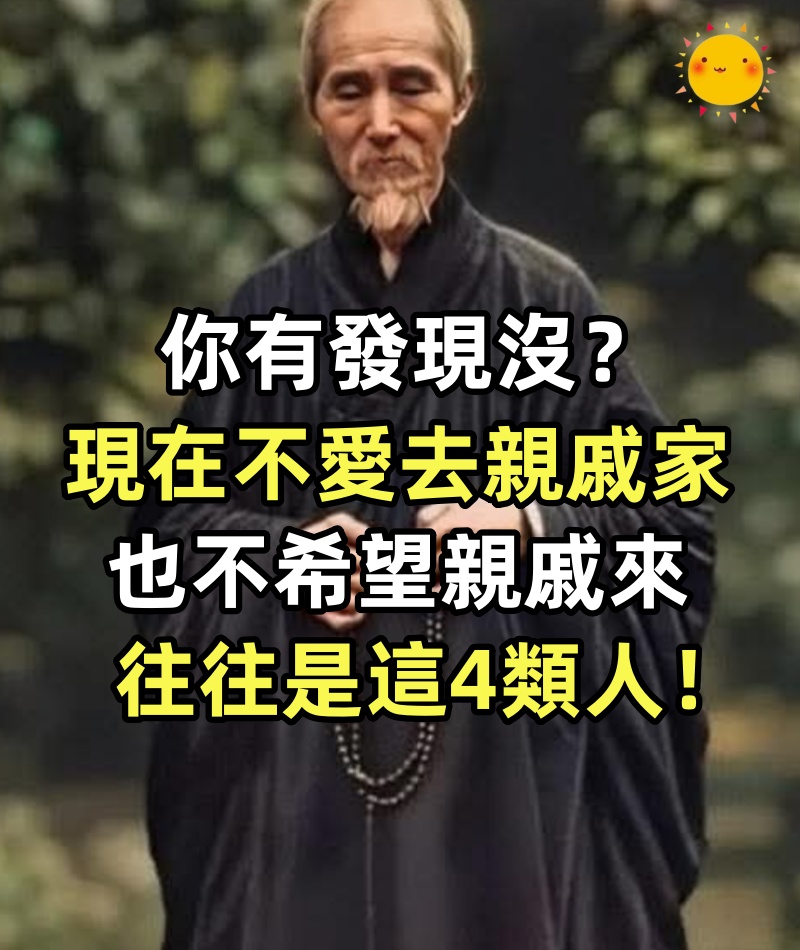早逝,也許是一種福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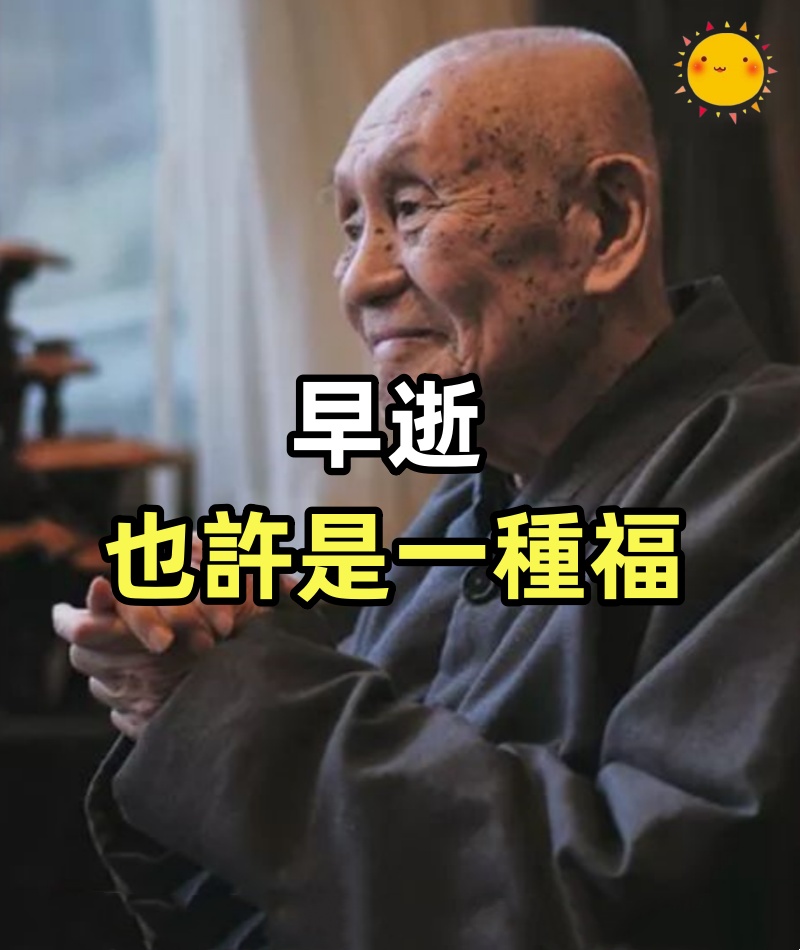
別只把早逝當悲劇:當「解脫」成為另一種可能,我的一點實感
說實話,看到別人把早逝定義成絕對的不幸,心裡總有些不太一樣的感覺。

不是因為我冷漠,而是因為我親眼看過兩種極端的人生:一個活到九十卻多年臥床腐朽,一個三十二歲離開卻留下了安靜的解脫。
兩種結局放在一起,讓我不得不去問,生命的好壞能不能只用「長短」來衡量。
我先生走得很早,連我自己都還在適應他的缺席。
他病了十幾年,最後不能走路,也不能平躺睡,吃藥的副作用和併發症像黑雲一樣籠罩著他。
剛走那會兒,我恨天、恨命,恨不得把他搶回來。
後來我做了一個夢,他在夢裡對我笑,說他好了,能走路了,年輕了許多。
那一刻我就知道,他是解脫了。
不是我麻木,而是看見了他從長期磨難中得到的那份安寧,我開始學著把失去當成另一種完成。
同時,我身邊也有另一種命運的縮影。
姥姥在八十歲時摔倒後癱瘓,八年裡孩子們從最初的盡心照料到漸漸推辭,最後她幾乎成了床上的陌生人。
這種被慢慢剝奪尊嚴的長壽,讓人心裡翻騰不止。
我常想起古人一句話:壽則多辱。

大家都嚮往長命,但若晚年只剩下病痛和被動的依賴,長壽未必等於善終。
把這些具體的個案放在更大的視角裡思考,我開始把「早逝是福」當成一種可以討論的命題,而不是一句冷冰冰的結論。
玄學裡講靈魂來世要完成的課題,現代心理學講意義建構,社會學講家庭資源與照顧負擔。
把這些東西合在一起看,早逝有時意味著:一個人完成了他這世間必須承受的那部分學習或救贖,從而離開了更長時間的痛苦;而留在人間的親人被迫去直面生活的重擔、理清情感、重新分配資源,往往也會因此覺醒或轉變。
霍去病被常拿來當作「使命完成」的例子,他的故事在我看來不是鼓吹死亡,而是提醒我們,生命的意義常常是與完成度有關,而非單純的年數。